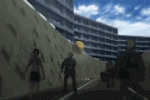下午的那一場戲

散文
十月的島嶼,陽光露臉時總顯得格外明晃敞亮,隱約聽得麥克風斷續的放送幾聲電子餘音。 秋收酬神時節,是祖師廟在熱鬧。而能穿越島嶼這鋪天蓋地顛顛季風的,就只有電音配樂的歌仔戲。
循着聲音,來到了社區廣場,紅藍塑膠棚子被吹得鼓鼓,間歇的凹凸起伏着。一旁紅烙烙的炭火,彼此依偎在鐵箱內,烘暖的空氣中滿是蒜醬香的誘惑。架上一邊是油潤香腸,另一邊是飽滿的米飯大腸,老闆精確的火候溫控,熟練似表演地轉動每根香腸,米飯大腸。它們也像是迸開了心事,滋滋作響的說着,選我,選我,像益智節目中的小學童,擠眉弄眼的爭相指着自己。
我不急着去哪了,坐下來聽戲吧。雖然不愛廟裡的嗩吶聲,總太「聲聲入耳」,但此刻的氛圍與情調實在很有感覺,所以就近選一個邊邊的位置坐定,不擋後面避風看戲的長者們。
稀稀落落的幾個觀衆,都安靜的聆賞。該是對戲碼陌生,想迅速入戲,也或許是舞臺音響太強勢,麥克風擴音壓制所有,讓彼此交談徒勞了。
午後已有冬日寒意,斜風吹過廣場,我習慣的壓低一下帽子,想起了錢穆先生說:那些忘不了的人與事,纔是真生命。
是啊,上次看歌仔戲是國小時。細究這遙遠距離的緣由,是因不愛狂風亂髮的狼狽樣,怕頭痛,總嫌臺上的一切太現代化,太嘈切,擾得我神經緊繃,心亂如麻。那此刻這股驅力,是兒時思念傾巢而出的使然。
我習慣先搜尋着舞臺。頭頂抓綁着一球頭髮,瀏海整齊的音控小哥,忙碌的一人全攬所有的鑼鼓鈸聲。對照起從前,那樣的戲臺角落,至少是一排三人的管絃絲竹樂師。舞臺邊框的電子霓虹看板,字節奔跑着~~農曆 歲次壬寅年 十月初三 今日午場 黃巢亂唐。
正中央兩幅布幔,前幅是廳堂,後幅是山水,隨着情節樂聲迅速變換着,廳堂那幅褪色成薄涼淡紫,草莽青綠的那幅也如避世歸隱,淡出於蕭瑟,也歷史,也滄桑。倒是正上方〔明華園天字號〕的招牌,紫氣東來,瑰麗逼人。
回首看戲過往,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着舞臺上的角色。生旦妝容都細緻,眉眼的描繪也鮮明,體態勻稱,聲音飽滿,唱腔圓亮。 雖看得出年紀,但每個人都維持着一種舞臺的魅力與風采,那是不需任何對於美麗的包容,就能讓人心生敬佩,由衷稱許讚賞。
對於歌仔戲戲碼,我仍停留在小時候的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,薛丁山與樊梨花,陳世美棄糟糠妻。那時的許多個寒夜,村子大人小孩都夾抱着木頭小板凳,手插褲口袋,成羣結隊走到廟埕前看戲。偶爾也 「追劇」,那是自家村莊演完,劇團預告着行程,我們一往情深地再到鄰近的鼎灣,中西,和路程近一小時的沙港村,一檔一檔的追着。
村子的戲棚正前面,會有幾排座位,是用廟裡平時拜拜放供品的長長坪板和空心磚堆架成的,專門給小孩看戲的特別座。大人則是由自家拿出圓板凳,長條椅板,天尚未黑時,就先去佔位置,給自己,也幫朋友佔。 那種大夥坐一起,有着說笑的歡樂,是無可取代的。佔完位置,再回家速速洗澡吃飯,香噴噴又舒服地期待着一場感官與心靈的饗宴。戲大約是從七點半開演,十點半散戲。 我們回到家都快午夜了,只能說演戲的看戲的都瘋魔了。平時的八點鐘,全村已靜寂,唯風聲情癡,守夜至天明。
我之所以記不得太多的戲,是因爲當時年紀小,無法理解那鏗鏘有力的忠孝節義。因爲我坐在前面,尷尬的個子總太高擋人了。我不安又無聊,就躬着身子穿過舞臺正下方,到戲園子帆布開口處,看着演員們上妝聊天。有時活動中心剛好連着戲臺(當時慣用它來充當全體團員們睡覺吃飯的地方),我看着幾個大小孩子,在一牀牀相連接的棉被枕頭上,有的爬,有的跑跳,互相追逐玩耍。在一旁洗碗整理的阿姨,時不時的擡頭看顧着他們。一兩個背心穿着,衣服直接寫着兵卒的大孩子,手持關刀站在入口處,準備聽到鑼鼓換場聲,就要越過戲棚搭繩,跳上舞臺,跑跑龍套串串場。
長大後,有個畫面時常縈繞我心。一次,一個穿着戲服的旦角,下臺後直奔活動中心內,攏來孩子,解開衣襟,讓孩子吃奶,隨即又在棉被下摸出一包煙,打火機,深深吸了一口,吐出一圈圈的煙,再慢慢的抽着那根菸。我急急退開,怕被罵,因爲自己的窺視,因爲她的裸露。當時記憶中,村子沒有一個女人會抽菸,哪怕是高懸着菸酒牌的雜貨店老闆娘,也不曾抽着煙。
綢緞錦衣的女旦,斜靠捲起的一座棉被小山,兜着倉皇接收着汩汩乳汁的嬰兒,孩子嘴角流淌滿溢着油膩。吸吮之必要,生活之必要,迷濛之必要,那一刻,她,比起臺上任何一次的扮相都美,毫無保留,簡單幹淨。
年幼無害,所幸未被驅趕,盡看戲棚下,後臺內,人事物。目光所至最鍾情的就屬那年代女生都愛的化妝箱。生旦們身着素潔白淨的硬領脖圍,端坐鏡前,挑起幾絲鬢髮,醮着髮膠,沾黏整齊的勾勒到雙頰,幾分柔媚,幾分英氣,盡付其中,不聽他們的聲音,真讓人雌雄難辨。一旁珊瑚紅,正桃紅的化妝箱,是個寶盒,承載映現所有青春姣好與年華。
箱前有一對可兩邊滑開的鎖釦,恰如久遠年代的行李箱,輕輕一撥,箱蓋就會自動彈跳開來。珠光白緞面的縐褶襯布,襯出明亮的鏡子,箱蓋穩穩的立靠着,各式顏料,長短粗細的彩筆,大小粉撲,吸附了鮮豔的脂粉香,金色蜜粉只需輕輕一推,微微一刷,嫣紅漫漶,迆灑至耳際雲發。
生旦們起身罩上外衫,整束髮網,戴穩配飾,或珠花,或雉翎,或紗帽…。整個後臺立時晃動擁擠,大家自動讓出,那擡眼便是姿態,步伐已成場面。粉墨登場的前戲,春色已撩亂,人心已騷動。
歌仔戲演出的日子,若遇寒假時,我早早就會跑到海邊,觀察着戲班們的日常。在戲團裡最有壓力的,大概是武生,武將。 吃午飯前,他們先是運氣練功,再拿起兵器,長刀長棍,揮舞跳躍,幾個側滾翻,前滾翻,後空翻,再跑上幾小圈。冬日裡,練出一身汗水淋漓。樂師們則在一旁抽菸閒聊;女角們在活動中心內燒水,盥洗,顧孩子;煮菜阿姨清理市場菜販送來的魚肉蔬果。 空氣中,海風鹽煙中,飄着辛辣的蔥韭姜蒜,人聲擾嚷鼎沸。陌生人,新鮮事,我的村子多了難得一見的活力生氣。
歌仔戲團拔樁,拆棚,離開之後,得空時,我會將自己西瓜皮的短髮,抓出鬢角,用口水沾溼貼於頰上,身披對摺的大花被套,在領口袖口處翻出一些素色內面,踩在嘎嘎作響的日式通鋪房內,水袖輕攏,蓮步輕移。 眼眸顧盼間,彷彿已是寒風中,那年的戲臺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