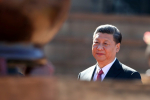百年包浩斯:革命狂飆年代的「左派美學實驗」

「所以我說,『包浩斯』(Bauhaus)到底是什麼?」圖爲馬塞爾.布勞耶(Marcel Breuer)所設計的包浩斯經典「瓦西里椅」(Wassily Chair)。 圖/Klassik Stiftung Weimar
2019年是德國「包浩斯」(Bauhaus)創立100週年,德國上下各種紀念活動不斷。
位於柏林、德紹、以及威瑪的三個包浩斯機構,聯合德國聯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特地創立了「2019包浩斯協會」,藉百年紀念的契機推動「包浩斯觀光」;寮國裔德籍建築師雷門特澤爾(Van Bo Le-Mentzel),甚至設計了一輛「包浩斯巴士」,於今年巡迴德紹、柏林、金夏沙以及香港四座城市,意圖藉由巡迴歐洲以外的城市,重新思考現代主義包藏的歐洲中心主義、殖民主義。
現今講到「包浩斯」,腦袋中可能會浮現幾個模糊的印象:德國工藝美學?極簡風格?或是已經成爲Word內建字體的經典包浩斯字體?
但除了這些已經成爲現代主義經典的美學形式之外,「包浩斯」究竟是什麼?它誕生的歷史內涵又是什麼?這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,動盪的威瑪共和講起。

2019年是德國「包浩斯」創立100週年。這個跟隨動盪的威瑪共和而生的美學,直到今日影響力仍遍及全世界。圖爲德紹包浩斯學院的入口。 圖/flickr@Chrstian Stock
▌威瑪共和的誕生:戰爭創傷與「新德國」希望
1918年,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,德意志第二帝國軍隊幾近潰敗。面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,和戰爭帶來的經濟緊縮以及饑荒,雖然帝國政府在同年10月進行改革,仍然無法平息全國上下積怨已久的情緒;10月底,基爾港水兵起義抗命,緊接着就像骨牌效應一般,引發了全國性的革命,大大小小的工人起義、共產式革命、以及左右派街頭武裝衝突接連引爆。
面對這樣的內部壓力,德皇不久宣佈退位。1919年1月,新選出的國家議會於威瑪集會,並公告《威瑪憲法》,德國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「威瑪共和國」於是成立。
《威瑪憲法》雖然是在革命以及街頭戰的砲火之下倉促產生,卻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。《威瑪憲法》是由新的國會多數黨——溫和左派的社會民主黨(SPD)——主導編撰,不但取消帝制,宣佈德國爲民主共和國,保障全民普選,更第一次將「福利國家」入憲。
動盪危機中,《威瑪憲法》似乎預示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新德國。一戰帶來的集體創傷,以及《威瑪憲法》對於新德國的應許,也似乎爲威瑪時期的藝術與建築,帶來某種與過去的「斷裂」。
在街頭戰的砲火下,溫和左派的社會民主黨(SPD)主導編撰的《威瑪憲法》也倉促產生。對「新德國」的應許以及一戰的集體創傷,這種「斷裂」爲日後包浩斯的誕生予以沃土。圖爲1919年的「斯巴達克斯團起義」(Spartakusaufstand)。 圖/維基共享
▌威瑪時期建築藝術:左派色彩的烏托邦理想
威瑪時期的藝術,是對於戰爭創傷的療愈、對於存在意義的追求、對於改變社會——多少帶有左派色彩——的烏托邦想像。包浩斯的創辦人——建築師沃爾特・格羅佩斯(Walter Gropius)——1919年時曾說道:
「今日的藝術家處在一個崩解的時代,沒有方向。他獨自站着。舊的形式處在廢墟之中,麻木的世界重新改組;舊的人類精神已經無效,並朝向新的形式改變。」
這是一種帶有焦慮的烏托邦主義。對於未來的美好想像,起源竟是戰爭的創痛、家國幾近崩解的狀態;與格羅佩斯同時期的藝術家與建築師,在威瑪共和始創的前期,多少都有這樣「帶有焦慮的烏托邦主義」爲底蘊。
「今日的藝術家處在一個崩解的時代,沒有方向。他獨自站着。舊的形式處在廢墟之中,麻木的世界重新改組;舊的人類精神已經無效,並朝向新的形式改變。」威瑪共和始創前期,與格羅佩斯同期的藝術家,多少都有這樣「帶有焦慮的烏托邦主義」爲底蘊。圖爲社會民主黨首領之一的謝德曼(Scheidemann),在德國國會大廈西陽臺,宣佈「威瑪共和」成立。 圖/維基共享
建築師布魯諾・陶特(Bruno Taut)1919年繪製一系列名爲「阿爾卑斯山建築」(Alpine Architektur)的建築想像圖,利用鮮豔的水彩,想像在阿爾卑斯山上,沐浴天光下、晶瑩剔透的水晶建築,即是一種在經歷殘酷的大戰後,想要逃離戰場殺戮,對於靈性與共和大同的祈望。
在戰後烏托邦式的表現主義之後,經濟、政治局勢較穩定的1920年代中後期,更衍生出了「新即物主義」(Neue Sachlichkeit)。不同於表現主義表現內在情感、反映恐懼,新即物主義的藝術家們轉以更冷靜、客觀、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檢視德國社會的狀態,並更積極的投入社會民主黨主導的社會改革。
例如陶特就在1920年代中期,爲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各級地方政府,設計了一系列現代主義的社會住宅,成爲後世社會住宅的典範。這些社會住宅以現代主義的精神,爲威瑪時期大批的白領階級量身定做,以節儉的形式、有效率的空間,強調「光線、空氣、太陽」的整潔生活。之中最有名的,當屬坐落柏林的「Hufeisensiedlun」社會住宅。
陶特就在1920年代中期,爲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各級地方政府,設計了一系列現代主義的社會住宅,之中最有名的,當屬坐落柏林、馬蹄鐵形的「Hufeisensiedlun」社會住宅。 圖/維基共享
▌格羅佩斯、包浩斯、與烏托邦精神
包浩斯的創辦人格羅佩斯,同樣抱持着這樣兩種態度——烏托邦式的理想,與實事求是的「新即物主義」精神——來面對新德國、新社會帶來的挑戰。威瑪共和本身就是一個巨型的社會實驗,在這個歷史脈絡下,包浩斯創立的精神也是如此。
1919年,格羅佩斯在威瑪創立包浩斯學院。格羅佩斯將包浩斯設計成一所綜合性的藝術與設計學院,藝術家與工藝家在同一個屋檐之下共同學習、工作。在包浩斯學院,格羅佩斯希望揚棄尼采式的個人主義神話,強調社會主義式的集體主義。而不管是於威瑪創校,或是日後遷往德紹,包浩斯都受到地方執政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支持。
威瑪共和本身就是一個巨型的社會實驗,在這個歷史脈絡下,格羅佩斯在1919年創立的包浩斯學院,其精神也是如此。圖爲德國羅森泰瓷器(Rosenthal)今年舉辦的「激進當代」展。包浩斯創辦人格羅佩斯(圖中肖像)曾與羅森泰跨界合作,設計經典的「TAC」茶具組。 圖/美聯社
格羅佩斯期望將傳統的高等「藝術」與實用「工藝」兩者之間的界線消弭,希望美學與實用性能「有機」地結合。學生們不但要學習如繪畫、雕刻等等的傳統藝術項目,更要學習不被學院派看重的工藝,例如金工、陶藝、紡織,或是攝影這類的新興媒材。於是在包浩斯前前後後任職的教師,跨越各個領域,從畫家康丁斯基、保羅.克利,到攝影師拉斯洛・莫侯利-納吉(László Moholy-Nagy)以及建築師密斯(Mies van der Rohe),各個都是現代藝術界舉足輕重的人物。
他也希望打破現代學院之中僵固的「教授」與「學生」階級區分。他取消「教授」的頭銜,而恢復中古工藝行會的師徒制,除了希望提倡更親密的師徒關係,更希望喚起對於中世紀的美好幻想:工匠不是對於工作疏離的現代工人,而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心力、驕傲於自己作品的匠人。
在這樣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理想之下,包浩斯創新了藝術教育的內涵。除了講求打破藝術疆界、重視綜合媒材的使用之外,每個學生都要上「形式課」(Formlehre),要求學生像孩童一樣,「打掉重練」,從最基礎的元素「玩」起,重新認識基礎的色彩、材質、形狀,要求學生,忘掉歐洲僵固的學院派傳統,確確實實地革新了藝術教育。
包浩斯一衆大師(德劭時期)。左四爲莫侯利-納吉(László Moholy-Nagy)、左七爲格羅佩斯(Walter Gropius);右四爲保羅克利(Paul Klee)、右五爲康丁斯基(Vassily Kandinsky)。包浩斯學院的誕生背景以及包浩斯學派,帶有左派色彩。 圖/Bauhaus-Archiv
▌實事求是的現代建築
在具烏托邦理想的藝術教育之外,另一方面,格羅佩斯也抱持着「新即物主義」的實事求是精神,重新思考藝術、工藝、建築與現代工業社會的關係。身爲建築師的他,認爲建築是所有藝術的集大成之處,是貨真價實的「整體藝術」(Gesamtkunstwerk)。建築這種「整體藝術」的訴求,是達到功能、質感最完美有機的結合。但這種有機的結合要如何達成呢?他寫道:
「建築在前幾個世代變得感情用事、追求審美、裝飾性…我們要揚棄這種建築。我們要創造明確、有機的建築,其內在邏輯要外顯並赤裸,不受騙人的外觀與雕蟲小技阻擋;我們要可以適應充滿機器、收音機、汽車的新世界建築,功能可以明確在形式上辨認出來的建築。」
格羅佩斯的現代主義信條就是「形式跟隨功能」的「功能主義」。他拒絕古典式、學院派建築的虛假美學以及冗贅裝飾,他認爲建築的美感應來自功能,建築師不應該依從任何武斷的美學理論,而要從最基本的功能下手。
他也認爲建築要「讓材質說話」,讓材質就是材質,不應「模仿」任何其他東西,而他認爲最適合現代的,當然就是工業材質——鋼鐵、水泥、以及玻璃;建築也不應該有任何的歷史典故,不模仿古希臘或是中世紀,而是完全指向「現代」。這就是他所認爲的「有機建築」。
格羅佩斯的現代主義信條就是「形式跟隨功能」的「功能主義」。圖爲由格羅佩斯設計建造的德劭包浩斯學院建築,至今仍是現代主義建築的經典之一。 圖/法新社
除了建築形式之外,更重要的是,格羅佩斯認爲建築必須符合當代的「時代精神」,對他來說,就是機械化與大量製造。在包浩斯的學生,必須認清現代社會不可逆的事實——他們設計的工藝產品必須可以大量製造,建築必須使用預先製造的建材以及標準化的模組。
格羅佩斯自己最著名的建築作品,是位在德紹的第二代包浩斯校舍。德紹的包浩斯校舍,忠於他自己的理念,以「功能」作爲設計方針,三棟主要的校舍分別具有不同的功能,並由架空的天橋連接。三棟主要建築之間打破古典學院式的對稱,呈現一種動感的趣味。在建築工法上,格羅佩斯把承重牆隱藏起來,把外表留給一整面、不間斷的玻璃帷幕,輕盈得像是浮在空中一般。德紹的包浩斯校舍,呈現了格羅佩斯對於功能、媒材、美學、現代性之間的深刻思考,至今仍是現代主義建築的經典之一。
在德紹,格羅佩斯更受到市政府的委託設計了大型的社會住宅羣落(Bauhaussiedlung Dessau–Törten),以解決住宅不足的問題。一如同時期的陶特,格羅佩斯跟包浩斯學校擁抱了新德國帶來的挑戰,以建築進行社會改革。格羅佩斯以工業生產線概念來設計這個住宅羣落,一切模組化,使用低成本、可以快速組裝的預製組件來建造——只有現代的建造工法,才能解決現代德國的問題。
格羅佩斯受德劭市政府的委託,設計了大型的社會住宅羣落(Bauhaussiedlung Dessau–Törten),以工業生產線危概念設計,一切模組化,使用低成本、可以快速組裝的預製組件來建造,以解決住宅不足的問題。 圖/Dessau Junkers Trail
▌右派、納粹的攻擊,以及包浩斯的重生
一如在曇花一現的威瑪共和時期,綻放的種種現代主義藝術與建築流派,包浩斯從創始以來,就不斷受到傳統右派,以及後來納粹黨的攻擊。
1925年,包浩斯受到威瑪在地右派的猛烈批評,導致格羅佩斯不得不遷校。對於包浩斯的指控包括了「文化頹喪」、「布爾什維主義」,對以古典教養與大文豪歌德爲傲的威瑪當地仕紳來說,包浩斯的左派社會實驗,像是試圖要顛覆德國的共產布爾什維主義一般危險,而包浩斯所提倡的現代主義,更彷彿要拔除德國的文化傳統。
1925年遷校至德紹之後,隨着納粹黨逐漸崛起,包浩斯受到的指控變本加劇,而且批評越加與「國族」掛鉤。批評者認爲,以包浩斯爲代表的現代主義「沒有國界,沒有對於國家的忠誠,沒有根,沒有文化」,是一種「遊牧民族式」的建築。
對威瑪當地右派來說,包浩斯的左派社會實驗,像是要顛覆德國的共產布爾什維主義一般危險,而包浩斯所提倡的現代主義,更彷彿是要拔除德國傳統的「文化頹喪」。圖爲格羅佩斯的作品「三月之死紀念碑」(Monument to the March Dead),紀念在「卡普政變」(Kapp Putsch)中死去的工人。1936年,納粹政權以「頹廢藝術」爲由,摧毀紀念碑,二戰後才行重建。 圖/維基共享
這種指控就跟當時對猶太人的指控完全契合:猶太人效忠「國際主義」、污染德國血脈。甚至出現了荒謬的「屋頂說」,認爲真正滋養自德國「血脈與土地」(Blut und Boden)的房舍,要有斜屋頂,那纔是真正的「家」(Heimat);強調功能的平屋頂現代主義建築,屬於沒有靈魂的機械世界。
1931年納粹黨掌握了德紹市議會後,勒令包浩斯關校。當時的校長密斯,雖然於1932年在柏林重新開校,但在1933年納粹全面奪權之後,包浩斯便被迫永久關閉。包浩斯就如其他的現代主義前衛藝術一樣,被納粹打爲「頹廢藝術」(Entartete Kunst)。
不過包浩斯並沒有就此葬身。納粹奪權後,包浩斯許多成員,像其他威瑪時期的猶太或左派知識份子、藝術家、科學家一樣,陸陸續續逃亡國外,許多人在新大陸找到桃花源。在美國,格羅佩斯創立私人建築公司執業,然而持續發揚包浩斯的,卻是曾在包浩斯任教的攝影師莫侯利-納吉,以及最後一任校長密斯。
納粹奪權後,包浩斯許多成員,像其他威瑪時期的猶太或左派知識份子、藝術家、科學家一樣,陸陸續續逃亡國外。圖爲New Bauhaus在美國的第一個新據點「Marshall Fields Mansion」。 圖/維基共享
莫侯利-納吉與密斯落腳美國「建築之都」芝加哥,並在1937年成立了設計學院(Institute of Design),後來整併成爲了伊利諾理工學院(IIT),校舍建築幾乎全爲密斯一手設計。 圖/維基共享
莫侯利-納吉與密斯落腳美國「建築之都」芝加哥,並在1937年成立了設計學院(Institute of Design),後來整併成爲了伊利諾理工學院(IIT),校舍建築幾乎全爲密斯一手設計。這座學校被暱稱爲「新包浩斯」(New Bauhaus),莫侯利-納吉與密斯延續威瑪共和的包浩斯精神,繼續在芝加哥教育英才,並讓芝加哥成爲戰後現代主義建築的重鎮。
包浩斯在一戰的陰影下誕生,帶着烏托邦式的理想,以社會實驗的精神,不僅僅想要改造藝術教育、更想要藉着工藝以及建築改造「新德國」。雖然包浩斯就像威瑪共和這場巨型的社會實驗一樣,最後葬送在納粹手中,但塞翁失馬、焉知非福,納粹的迫害反而讓流亡的包浩斯,理念散佈到全球。
在美國的密斯,戰後成爲現代主義建築的第一把交椅,「少即是多」的理念以及經典的玻璃帷幕大樓,不知道影響了多少城市的天際線。百年以來,不管是德國工業設計師布蘭德(Marianne Brandt)的茶具組,或是布勞耶(Marcel Breuer)的「瓦西里椅」(Wassily Chair),這些上承包浩斯的設計早已成爲經典款,影響日後工業設計。包浩斯原本是帶有顛覆性的建築與社會革命,時至今日,影響之廣,早不知不覺滲入我們生活之中,無處不在。
走過一百年,雖然包浩斯就像威瑪共和這場巨型的社會實驗一樣,一度葬送在納粹手中,但塞翁失馬、焉知非福,納粹的迫害反而讓流亡的包浩斯,理念繼而散佈全球,影響工藝建築設計美學至今。 圖/Bauhaus1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