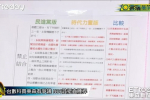【當代散文】黃梵/時代之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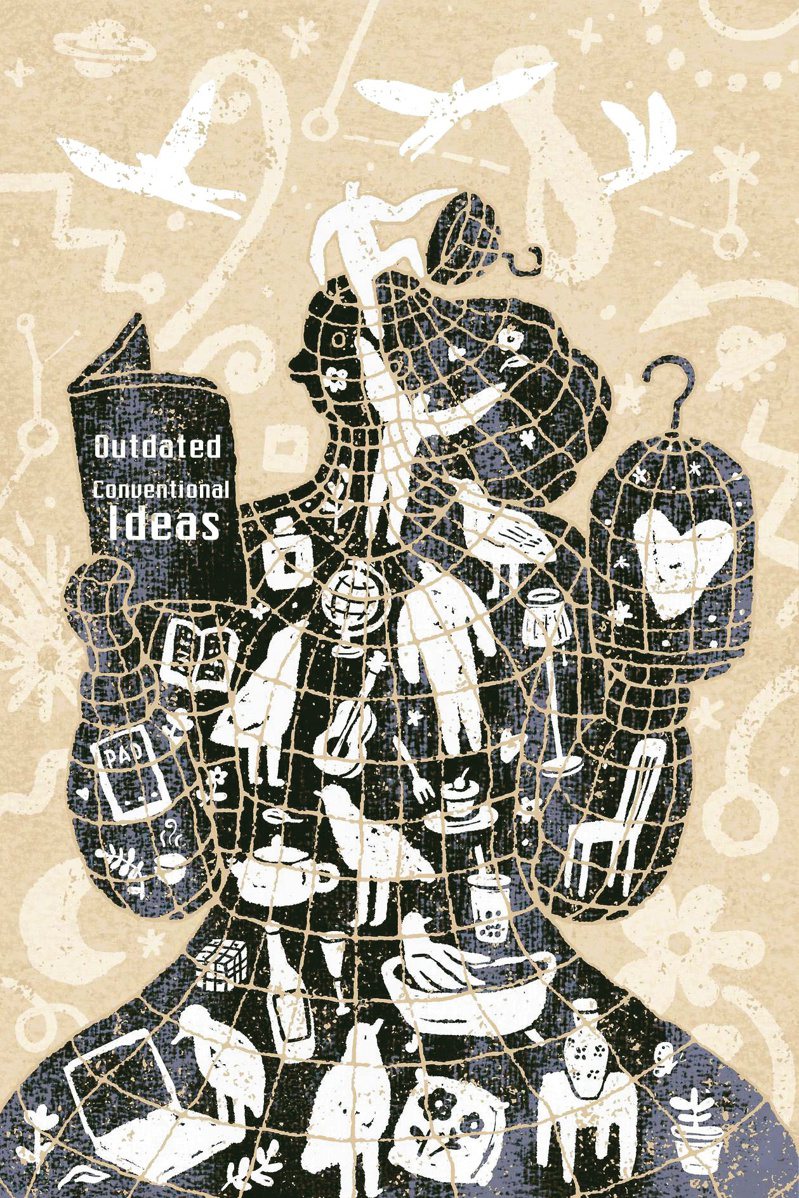
時代之力。(圖/想樂)
1
我廚藝不精,偶爾救急下廚,等家人圍桌動筷子,我的心理已變得微妙。母親是家裡的「公知」,專以挑刺爲己任,我做的菜在她口中的風評,向來不高。不是油多菜生,就是肉老魚腥,或鹽多醋少。她垂着眼皮批完,會揚起眉毛,把我的思緒,引向她做的菜,那裡已站着一排讚詞。她並不知道,評點我的菜時,她爲何會情不自禁地誇自己,但我心知肚明。
衆人以爲,信徒唸經,是爲了理解經義或施展法力,固然有這樣的考慮,但我以爲,唸經真正的指向是自己,那是遮罩外界聲音,用經文之聲,日日肯定自己的功課。人出世或選擇信仰,不是一蹴而就的,需要不斷暗示自己,「這麼做是對的」。人走入世還是出世之路,並不取決世俗或信仰本身,而取決人能否從中肯定自己。日日唸經,既含着說服自己,也含着肯定自己的魔力。
母親的日日挑刺,或自我誇讚,何嘗不是一種唸經?
父親去世後,她來南京和我一起生活。隨着日漸衰老,她能找到的肯定自己的事物,越來越少。初來乍到的前兩年,她甚至期待涉足我的領域,並得到肯定。記得有一天,她突然問我寫了什麼,我說剛寫完一篇詩評,她馬上叫我給她看。我照實說,她不一定看得懂,提議還是看我的詩。沒想到,她執拗起來,認爲我太小看她,說這世上還沒有她看不懂的文章。沒轍,我只好把詩評列印出來,交給她。以前她讀我的作品,有固定不變的環節:她會選擇空閒的一天,專門找我聊天,補上口述的讀後感。
那天之後,她一直沒再找我補上讀後感,我也不再提詩評之事。
再後來,她聽家人勸告,去上老年大學,成了班上極受歡迎的高齡楷模。她顯得年輕,健康敏捷,令同學驚訝、膜拜,成了學校神一級的人物。常有人主動搭訕,問她是否就是那個傳說中的老太?她向我轉述他人的種種推崇時,喜不自禁。
很快,她對人的態度,有了內外之別。對外人,她通情達理,永遠說他們好。對家人,她處處挑刺,總嫌家人不如外人。剛開始,我不懂這是她內心的需要,苦惱過一陣子。直到某天,我才明白這天壤之別的對比,從何而來。我父親一輩子心悅誠服地讚美她,不光爲抵消家史帶給她的失敗感。我的外公,她的父親,是四川農村的鄉紳,土改後,她不再回家,成了一個走遍大江南北不肯歸根的人。我父親的讚美、呵護,讓她有醉意似的幻覺——至少她是斗室內的主人,尚能把握斗室內的命運。被家史吹滅的種種希望,全部轉爲她對來自我父親讚美和呵護的日日索求。
我父親一走,原本由父親日日唸的「讚美經」,無人再念。我曾試過數次,均以失敗告終。母親不信我說的讚美話,我也做不到像父親那樣懂她,總撓不到癢點。有次我剛說完讚美話,母親忍俊不住,直截了當地說,別再哄我了,你只是想哄我高興而已,我不需要哄。她說的沒錯,她需要的是讚美,而不是哄騙。
數學中有個哥德爾定理,是說要判定某系統的好壞,若不跳出該系統,是無法判定的。我意識到,哥德爾定理出現之前,人們已在踐行該定理的主張——人人在乎自己在別人口中的風評。人對自誇不信任,纔在乎別人的誇讚。即使有人喜歡自誇,也是喜歡在別人面前自誇,不喜歡獨自對着牆壁自誇。他試圖通過自誇,來影響別人對他的評價,說到底,仍是對自誇的不信任。
母親對我誇讚的不信任,讓我明白一個道理,凡和她有血緣關係的人,統統被她納入「我」的範圍,凡「我」對「我」的誇讚,都不足爲信,不足爲貴。
2
沒有什麼能像美那樣,誘惑心靈,它也成爲人飽食之後,最願意追隨的事物。可是美,一天也少不了物質的護航。一旦匱乏,那些支撐人的美,就會被無禮甚至粗野改變。
母親至今曬衣服,仍不經意會顯露舊時代的蠻力。曬褲子時,不只把褲袢套在衣架鉤子上,她還會把褲子旋轉一圈,將鉤上的褲袢擰成麻花,方纔心安。等褲子曬乾,原本平直的褲袢,就變形成三維的蛇,十分難看。
母親爲什麼要如此虐待褲袢?她把褲袢變成立體的蛇背後,是來自舊時代的恐慌、不安——她太擔心褲子被風吹落,教人撿走!在買衣服需要布票,布票永遠不夠用的年代,遺落一條褲子,是天大的事!
天大的事還包括,能否讓衣服的漂亮保持得更久?母親眼裡的太陽,是恩人也是小偷。它幫母親曬乾衣服來施恩,又悄無聲息偷走衣服上的顏色,讓留在衣服上的色彩,越曬越淡。母親已有五十年與太陽鬥爭的歷史,她帶着歲月賜予的智慧,來到南京。逢到全家要曬衣服,滿陽臺就成了她智慧的用武之地:不論內衣外衣,一律把內裡翻出來暴曬。如此對待外衣,家人尚能接受,把內衣也翻出來曬,家人就接受不了。誰願意自己的內衣內褲,沾上細菌、灰塵、病毒呢?
家人把顧慮告訴母親,她倒爽快,馬上就改,只翻外衣,不翻內衣。但改變之力僅夠維持一次,到下下次,她的智慧又捲土重來。有好幾次,我代表全家提議,無論內衣外衣一律不翻曬,這樣好記。我強調,新時代的穿衣習慣已變,不等顏色曬淡,就需要換新衣,這同樣是爲了保持美觀。哪怕是這樣的「好記」,往往也只能維持一次。這麼看來,舊時代的智慧已變得深沉,深深沉入了母親的潛意識。
她潛意識中還有一個智慧:遇到比較髒的衣服,一律用開水伺候。那個年代的衣服,與那個年代的人一樣,比較簡單,少有羊毛羊絨類的衣服,用開水除髒真還管用。不知從哪年起,家裡已人手數件羊毛羊絨衫。母親常自告奮勇,和內人爭奪我和兒子的「洗衣權」。內人徹底放手的那一天,跟母親「約法三章」,其中之一是:羊毛羊絨衣物,一律不用熱水洗。母親第一次洗我和兒子的羊毛衫,十分成功,那時她腦子裡還掛着媳婦設的一根弦:不能用熱水洗。到第二次洗羊毛衫,時間已過去半年,我對她潛意識中的智慧,也失去警惕,以爲她會繼續「照章辦事」。沒想到,等羊毛衫洗完涼曬出來,我和兒子都傻了眼,各自最心儀的一件羊毛衫,下襬已縮到胸口,袖口已縮到肘關節,完全不能穿了。細問之下才知,她覺得男人穿的衣服髒,必須要用舊時代屢試不爽的開水「大刑伺候」,早忘了媳婦的「約法三章」。
母親慚愧不已,從此不敢再染指家裡的「高檔衣服」。我和兒子也只敢把耐折騰的牛仔褲交給她,穿褲子時還要對麻花狀或蛇形的褲袢,視而不見。一家人的內心,分明沉浸在兩個時代。舊時代並沒有死,仍在尋找衣服、器物、人事等,與新時代暗中角力。
3
年代常會偷走我們的包容之心,讓彼此的年代,暗中鎖着我們。
有一天,我就目睹了母親因年代而生的苦惱,她並不知,體內有暗中鎖着她的年代鐐銬。那天是保母不來做飯的週末,內人做完午飯,教我母親盛飯,沒想到,幾句再簡單不過的對話,竟對出了母親數日的苦惱。
母親盛飯時詫異道:「哎呀,飯做多了,我給你(指媳婦)多盛一點吧。」
內人勸阻道:「別給我盛多,我吃不了。」
母親爲難道:「那怎麼辦?飯要盛不完了。」
內人提醒道:「剩下又有什麼關係呢?!」
母親有些耳背,內人就提高嗓門重複了一遍。我距離她們兩步之遙,看見母親聽懂後,以微笑作答。
第二天,母親和我單獨吃飯時,抱怨媳婦昨天提高嗓門罵她。我凝視着母親生氣的臉,驚詫不已。昨天,我是她倆近在咫尺的證人,瞭然事情的來龍去脈,以爲那是一段完美的婆媳對話,以母親的微笑完美收官。哪想到,這麼簡單的一段對話,陰謀論竟也來打攪。母親讓我相信,媳婦對她有氣,才故意提高嗓門。
換了過去,我會耐心解釋,竭力消除誤解。那天,我內心卻生出絕望,不想多說一句話。我看見母親被罩在過去年代的陰影裡,我用再多解釋的陽光,也趕不走那片影子。本來量着肚子做飯,固然有違中國人的慷慨傳統,卻是她的年代餓出的節約技能。母親熬得一手好湯好粥,夏天熬的綠豆湯人見人愛。只是,她那項餓出的技能,仍像獄警一樣盯着家人的碗:她做綠豆湯能精準到每人一碗,一勺也不多。她常以沒有一點多餘自豪。偏偏內人和孩子來自衣食有餘的年代,等吃完一碗,意猶未盡,想再吃,鍋裡卻空空如也。
母親固守着她那個年代的計劃經濟,做綠豆湯之前,每人得上報肚子的容量,她將按需做湯。問題是,大家知道母親的斤斤計較,一旦報多,吃不了還得兜着走,所以,寧可少報。可是,食物總有迷人的時候,等你的胃明白需要再來一碗,等你明白需要把享受推上新的高潮,鍋裡的空蕩,卻讓一切的好興致,戛然而止。這時再琢磨中國人的「慷慨」傳統,纔會品出意味。
慷慨實在是對人性的體恤,它知道在一些歡愉的時刻,人性會結出浪漫的碩果,會非理性地打破定量、正常,這時,唯有慷慨方能侍奉之,憐愛之。慷慨是把不確定的人性之謎,包攬在它足量的供應中,使定量淪爲算計、斤斤計較。這樣的慷慨似乎該來自豐衣足食的年代,偏偏在貧困的過去,它也普遍存在。鄰居來借一碗米,奶奶一定拿最大的碗,將米裝到碗口後還要堆成小山。鄰居還米時也一樣,恨不能碗口之上的米山,比借時還高。他們都擔心自己借出或還回的,是一碗太標準的米:米剛好只夠到碗口。標準的量,會給人斤斤計較的小氣感。人們把碗口之上的米山,才視作慷慨的領地。
慷慨是以沉默表達的歡迎詞:歡迎再來借,或歡迎多吃!母親每一次丈量他人的肚子,無形中等於暗示他人:我這東西金貴,你得悠着點吃!以己需度人,和以人需度己,大概就是標準與慷慨之別吧。
母親事事堅持的「標準」,被家人戲稱爲「德國人的刻板和教條」,可能來自內心的孤獨。她小學時被迫離開父母,初中畢業後,隻身一人赴長春讀中專。此後幾十年待在西北,身邊的親人或朋友寥寥無幾,甚至闕如。無多少親密之人,供她用來練習換位思考,久而久之,同理心就消失無蹤。年輕時物質匱乏的記憶,除了讓身軀有對餓的警覺,更令同理心,再難有生長之機。